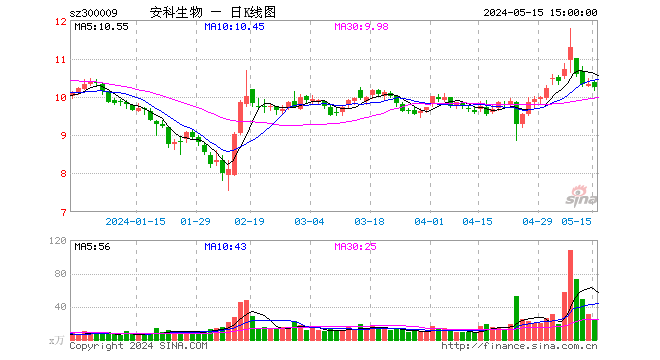来源:资识

1,财政政策的确出现了转向,但它的这种转向的效果对于市场主体的预期影响效果比较有限。
2,在新的形势下,实际上对利率不敏感的主体的信贷需求是被严重遏制住的。如果要想创造新的信贷需求,需要降息。
3,我们目前面临的这些短期问题,实际上有一个大的背景是,三大长期周期拐点的出现。
4,似乎从政策高层,就经济的稳定和发展,或者说经济的安全和发展,这两大政策目标上所赋予的权重发生了一些变化。
5,货币政策为什么迟迟没有降息?这背后也反映了政策层面的一些担心。
担心如果我们降息,在美国加息的背景下,有可能会触发资本流出中国,进而构成对国内金融体系的冲击。
以上,是重阳投资总裁、首席经济学家王庆4月20日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中,分享的最新观点。
王庆解读了近期经济的走势,三重压力叠加超预期,当前宏观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在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不达预期。
在这场交流中,王庆指出从中长期上来看,目前我们所面临的这些短期问题,实际上有一个大的背景,就是三大长期周期拐点的出现。
并且,王庆认为就经济的稳定和发展这两大政策目标的权重发生了一些变化,边际上更注重稳定和安全问题,对于发展问题相对有所减弱。
聪明投资者整理了演讲全文,分享给大家。
关于近期的经济走势和未来的预判,正如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一样,“三重压力”叠加超预期。
从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三重压力”这样一个非常精准的判断。
回顾过去一个季度,这方面的发展的确是超预期,使得“三重压力”变得更严重了,政策应对方面挑战也更多了。

财政政策有转向,但效果比较有限
首先,去年出现需求转弱的主要原因在于,宏观政策环境是非常紧的,我们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房地产政策都很紧。
尽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应对“三重压力”,标志着政策的转向,但从一季度的经济运行来看,这方面的效果并不明显。
财政政策的确出现了转向,但它的这种转向的效果对于市场主体的预期影响效果比较有限。
因为官方口径的财政赤字规模变化并不大,但实际上测算广义的财政赤字和隐含的财政脉冲还是挺大的。
去年财政脉冲的影响大概是负三个点的GDP,今年财政脉冲是正的,大概超过三个点的GDP,应该说(差距)还是比较大的,财政政策的确是在发力。
但是,我们财政政策的主要内容是在于减税降费,这对于保护市场主体,尤其是维持企业的活力是有帮助的。
可这个性质的财政政策刺激,它的乘数效应是比较小的,尤其是和直接的财政开支,比如说基础设施投资相比,对经济增长的直接效果要小很多。

缺少降息这样的货币政策配合
货币政策发力相对有限,尽管看到社融走势已经出现变化,但是,如果我们看社融的结构,实际上还是不容乐观的。
尤其是多轮信贷的增加,集中在非金融企业的中短期票据,最终需求尤其是消费端居民贷款需求是非常弱的,这说明有效的信用需求是不足的。
这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房地产,应该说房地产经过去年非常严厉的整肃之后,所谓病来如山倒,病愈如抽丝。
尽管各地房地产政策边际上在放松,但这种放松跟整个行业承受的压力比,只是非常边际的变化,难以出现实质性的扭转。
这就构成了一个问题,尽管货币政策在放松,相当于踩了油门,但是引擎发动机却不怎么工作。
因为房地产行业作为一个产业本身很重要,更重要的是,它一个信用创造的引擎,现在这个引擎没有工作。
房地产政策即使出现了边际放松,包括一些地区限购、限贷的政策调整,更多的是帮助房地产企业实现正常的资金周转。
但是,由于过去一年的冲击,这种资金周转流动性的改善,恐怕很难形成下一个阶段的实物量投资,进而对实体经济的支撑。
所以,就面临了这样一种情况,需求收缩本身尽管有政策的变化,但是效果并不明显,
在新的形势下,这方面的政策可能需要更大的动作。
以前的情况是有房地产周期在,有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在,其对利率不敏感,只要信用政策、信贷政策放松,就会产生新的一轮的信用周期。
但是在新的形势下,实际上对利率不敏感的主体的信贷需求是被严重遏制住的。如果要想创造新的信贷需求,需要降息,从而刺激对利率敏感的市场主体的信贷需求。
所以,如果没有降息这样的货币政策配合,恐怕我们在应对需求转弱这方面,政策效果是比较有限的。

供给冲击主要是来源于两方面
去年的供给冲击主要来源于两方面。
一方面是大宗商品价格上涨。
而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更多是来自于全球经济的后疫情复苏,对中国来讲不是一种通胀的压力,而是贸易条件恶化的冲击,包括对中下游企业成本的压力,实际上具有通缩性质。
第二个冲击就是疫情。
回顾过去一个季度,这两方面的冲击变得更加严重,目前来看一时无法缓解。
而预期转弱主要在于一些行业的政策,像是教培行业、互联网行业、医药行业的相关政策的确对市场主体的信心冲击比较大,影响了预期。
虽然说这方面的政策没有进一步加码,但是过去的一个季度多了一个来源,这个来源就是俄乌战争引起了市场主体对地缘政治风险的担心,多了一层冲击。
所以我们应对“三重压力”的挑战就更大了,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有更强有力的政策的支持。
如果预判趋势的话,我认为3月份看到的经济数据,很可能意味着未来一段时经济会继续走弱,今年经济的开局形势不容乐观,未来要想实现今年确定的经济增长目标也困难重重。

三大长期周期拐点的出现
那我们如何才能实现今年的经济增长目标?
从过往的20年,甚至30年的经验看,当政策层面发现了问题,并且做出了政策部署,我们的政策效果通常是比较明显的,也是比较有利的。
但是,从我个人的观察和分析看,今年很有可能是过去这么多年来,第一次出现政策效果不达预期的一年,因为“这次很可能不一样”。
我们把这个问题,放在一个稍微大一点的背景中来看待。
前面提到的这些短期的压力,实际上都发生在一个更大的历史背景中,这个背景就是中国经济从长期发展来讲,受益于过去这么多年的三大长周期。
第一,中国的人口周期。
第二,全球化的周期。
第三,科技周期,尤其是移动互联网为主的科技周期。
但是,站在这个时点前瞻性的看,似乎我们已经处在三大周期出现拐点叠加的时点。
人口周期毋庸置疑,对于科技周期,如果看互联网的人口数,渗透范围,以及技术进步的空间,似乎这种大的科技周期也出现了拐点,而俄乌战争似乎标志着全球化周期的结束。
如果说2018年中美贸易战是全球化“结束的开始”,俄乌战争似乎越来越让我们意识到全球化的结束。
所以,我们目前面临的这些短期问题,实际上有一个大的背景是,三大长期周期拐点的出现。

两大政策目标的权重发生了一些调整
再回到当前问题上,短期面临这么大的压力,又提出了一个相当高的经济增长目标,为什么政策力度和效果似乎不达预期呢?背后是不是有更深层的原因。
似乎从政策高层,就经济的稳定和发展,或者说经济的安全和发展,这两大政策目标上所赋予的权重发生了一些变化。
在这样一个短期和长期问题交织的环境下,可能在政策目标函数上,稳定和发展问题的权重有所变化,边际上更注重稳定和安全问题,对于发展问题相对来讲有所减弱。
这恐怕也是为什么我们迟迟没有见到更大的政策刺激,包括房地产政策转向和货币政策。
比如说货币政策为什么迟迟没有降息?可能背后也反映了政策层面的一些担心。
担心如果我们降息,在美国加息的背景下,有可能会触发资本流出中国,进而构成对国内金融体系的冲击。
此外,我们要维护国内金融体系的稳定,也要创造一个有利于以银行为主体的间接融资金融体系稳健的经营环境,维持相对正常的利率水平,维持金融机构的利差水平,有利于维护金融机构的盈利,也就是它的稳健运行。
所以,这些问题的考量,可能在政策目标上给予了更多的权重,也使得我们再应对“三重挑战”方面顾虑的比较多,给我们实现全年的经济增长目标带来了更大的挑战。

战略机遇期的重要条件或在变化?
最后我想再提一点,在相当长的时间以来,我们一直认为中国经济发展仍然处在战略机遇期。
而战略的机遇期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是,从全球范围来看,“和平和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的主题。
但在俄乌战争后,这个方面现在是否发生了变化?“对抗与安全”是否成为未来越来越不容忽视的重要暗流?这是我们当前关心的问题。
因为对这些大的问题的判断和形成的一些结论,很大程度上也会直接影响中短期的一些政策取向,也会影响市场主体的预期和信心。
你的专属投资礼包!更有百元京东卡、188元现金红包等你拿,100%中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