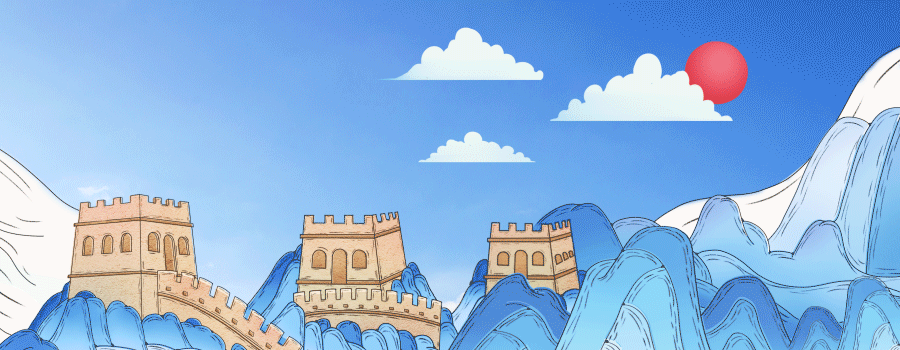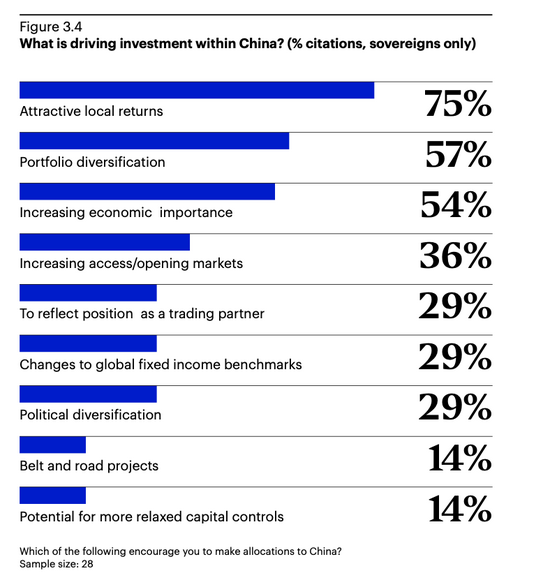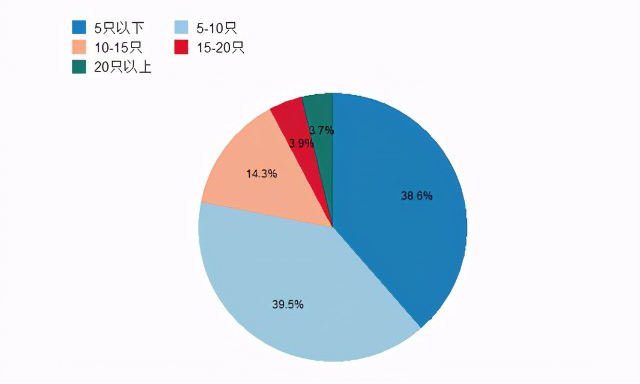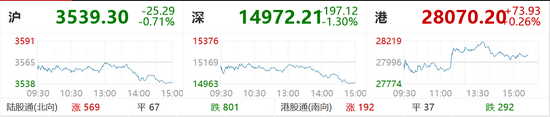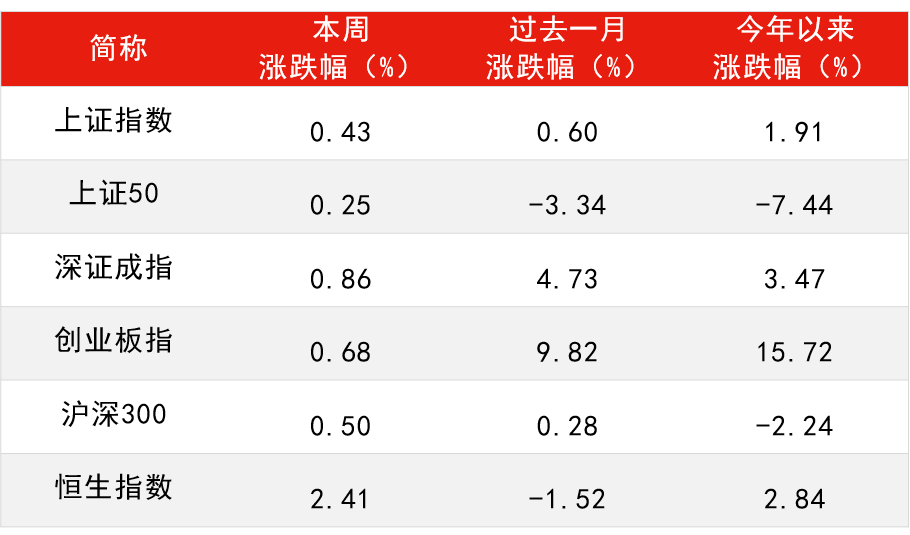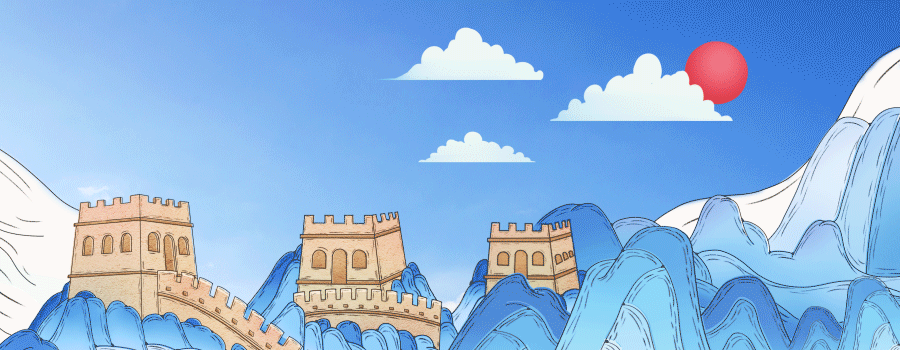古老的诗词典籍中,祖先们对万物色彩的感知,往往能让现代人惊叹:
桑叶初生、荷叶色黄,都可被称作“缃叶”;
夕阳薄雾笼罩远山所现紫色,名为“暮山紫”;

黎明时分高空天色,即“东方既白”;
黄河水色金黄闪光,称作“黄河琉璃”;

佛像面部金箔色,是为“库金”;
甘黄古玉色,也叫作“蒸栗”……
这些优美的传统色彩,来自天地万物的具象,也来自古人心灵的意象,是中国人独特的审美语言。它们是古人观察山川日月、草木鱼虫记录下的风雅,也是融于生活的诗意,更是缀连器物与文明的千年丝线。
每种中国传统色,不仅有极尽诗意的名字,也有着属于自己的独特故事。读懂了这些东方传统色彩,才能读懂古书诗句中的大千世界。
在花木蓬勃耀眼的夏天,正适合来一场视觉的郊游,悉心感受缤纷色彩带来的触动。
朱颜酡

拱手彩绘侍女俑西安博物院藏
朱颜酡,出自《楚辞》的醉后面色,原文是:“美人既醉,朱颜酡些”。
美人醉了,面上的颜色就是朱颜酡。颜色,这两个字最早是指面上的眼神和气色,所谓“视容”和“色容”,两者加起来就叫做“颜色”,而不是我们现在说的五颜六色。

古人讲颜色,面相的端正可以透视一个人的人品端正。面上的眼神和气色,讲究的是“见贤人则玉色”,贤德的人从内向外释放出玉一样纯粹的气质, 面上的眼神和气色像莹洁的玉色。
颜色两个字,就这样从“仪容气质”走向 “具象色彩”。
朱颜酡是醉后欢悦的颜色,从屈原到李白,吟诵的是这种颜色背后的愉悦心情,“落花纷纷稍觉多,美人欲醉朱颜酡”(李白)。中国传统色也有“酡颜” 的色名,本源就是“朱颜酡”。
宋徽宗写这种颜色如红玉:“灯影四围深夜里,分明红玉醉颜酡。”
留不住美好、浓烈的欢颜,刻画在记忆里,记忆是有颜色的,不妨沉醉。
银红

银红,似有银光的红中泛白之色。
银红的妩媚感觉,贯通古代文学作品。南宋词人蒋捷《小重山》咏:“银红裙裥皱宫纱”。《全元散曲》写到银红绣鞋:“手约开红罗帐,款抬身擦下牙床,低欢会共你著银红。”

明代《金瓶梅》和清代《红楼梦》也写到各种银红衣服和物件:
“那个软烟罗只有四样颜色:一样雨过天晴,一样秋香色, 一样松绿的,一样就是银红的”(《红楼梦》四十回)。
黄白游

黄白游,讲的是颜色,似乎又不是颜色,这正是中国传统色的微妙之处。
颜色可以来自天地万物的具象,也可以来自人类心灵的意象。之所以选择黄白游作为一种色名,因为它兼具了具象和意象两重美感。
写《牡丹亭》的明代文人汤显祖,文采斐然,章句拔群,然而仕途不顺。
友人吴序劝汤显祖到徽州去晋见退休在家的宰相老师许国,汤显祖却写了一首 《有友人怜予乏劝为黄山白岳之游》:“欲识金银气,多从黄白游。一生痴绝处, 无梦到徽州。”
黄白,既是具象的黄山、白岳(齐云山),也是意象的神仙梦;既是具象的黄金、白银,也是意象的富贵梦。

汤显祖的友人说的对:去徽州见见你的老师许国,黄白之间,气象万千,富贵袭人。
在汤显祖的心里,徽州的黄白已经不是神仙梦、富贵梦,而是他一生无法抵达的世俗之气,他选择了放弃: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请原谅我一生痴绝,不去徽州也罢,我这一生,既没有神仙梦,也没有富贵梦。
汤显祖之后,我们不但把黄白游看作黄、白中间的颜色,还看成我们挥之不去的神仙、富贵梦。
松花

松花,作为一种色名,至少上溯到唐朝。
如果不去考据松花的实物具象,它的颜色是扑朔迷离的:在网上查到的松花色,有黄中带绿的,还有浅绿色的。
松花可不是松果,它是松树雄枝春天抽新芽时的花骨朵。我在查证松花色 时,遇到擅用松花粉做滋补品的专家,她说:“抖落的松花粉像婴儿肤色一样娇嫩。”
然后,看到松花的实物,具象是最有说服力的,松花是嫩黄色。

唐人为松花色所倾倒,“轻如松花落金粉,浓似苔锦含碧滋”“自看和酿一依方,缘看松花色较黄”是唐代诗人李白和王建的名句。
松花色的笺纸,可以说是大名鼎鼎的中国传统色衍生品,所谓薛涛松花笺。薛涛之后,制作彩色笺纸成为雅事,明代戏曲家高濂在《遵生八笺》里说:“蜡砑五色笺,亦以白色、松花色、月下白色罗纹笺为佳,余色不入清赏。”
唐代诗人元稹在松花笺上回应薛涛的知音情意:“锦江滑腻峨眉秀,幻出文君与薛涛。”
卓文君和薛涛都是在川地生活的女子,都是敢爱的,她们的爱就像缱绻的锦江水、娟秀的峨眉峰。爱是滋补品,松花粉也是滋补品。抖落松花粉,古人专用一个“拂”字,仙气得很。
松花粉可以做松花酒,也可以做松花点心,据说食之身如燕、颜如春。北宋文人苏轼写过广告语:“一斤松花不可少,八两蒲黄切莫炒。槐花杏花各五钱,两斤白蜜一起捣。吃也好,浴也好,红白容颜直到老。”
天缥

天缥,貌似不熟悉,其实很熟悉的一种色名。
天缥是上古的说法,缥是 “青白色”,天缥是“天空淡淡的青白色”。说到这里,立刻想到“雨过天青云破处”,没错,很熟悉的天青色就是天缥。
天青色,不就是天空清澈的浅蓝色吗?其实,未必然。
青是很令人迷惑的颜色,从原本上说“取之于蓝,而青于蓝”,青色是取之于蓝草的蓝靛,蓝靛与蓝草相比,胜在质变。青金石的矿物色就是原本的青,天坛顶是这种青色。
同时,青色可能是青白色(缥),是青绿色(碧),是绿青色(葱),是青黄色 (绿),是青灰色(苍),是青红色 ,是深青红色(绀),是青黑色(黛),甚 至是黑色(黑)。
古汉语里出现一个“青”字,上面这些颜色都有可能,你会不会晕掉?
缥,跟青一样令人迷惑,所以有蓝色的“青缥”、淡蓝带淡绿的“碧缥”、 淡绿带淡蓝的“缥碧”、淡绿灰的“骨缥”、淡蓝微带红的“红缥”。

到底是什么颜色,摸摸头看看天。看看天,至少“天缥”的颜色判定是对的:如果天空像洗过一样,天缥是浅蓝色;如果“雨过天青云破处”,有大片云的天空透明度没有那么好,天缥是淡蓝绿色。
顺便说一句,“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做将来”是后周世宗柴荣说的,他的柴窑瓷是这般颜色,宋徽宗没有说过这句话,但他的汝窑瓷也是这般颜色。
玄天

玄,黎明的太阳跃出地平线前的天色。
玄与是相对的色名,取自黎明的天象。玄不是纯粹的黑,而是黑中透红,所以《说文解字》里说“玄,黑而有赤色者为玄”。

《道德经》里有一句很著名的话:“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辨析、解读玄的具象和意象:玄既是天象的特殊时刻,黎明将至的天色,又是宇宙的开窍觉悟,大道将启的原始。
玄与纁,都是人类敬畏天地、观察天象而来的。因为敬畏天地,玄、纁就成为第一重要的礼服颜色,上玄下纁的衣裳色彩搭配是周代服色制度的顶级设计。自天子往下,诸侯、大夫、士在祭祀和婚礼时都是上衣为玄色、下裳为纁色,身份区别在于衣裳的章纹不同,有资格出席的祭祀等级不同。
窃蓝

窃蓝,汉语颜色词里的第一个浅蓝色,出自《尔雅》:“春扈,鳻鶞。夏扈,窃玄。秋扈,窃蓝。冬扈,窃黄。桑扈,窃脂。棘扈,窃丹。行扈,唶唶。宵扈,啧啧”。
扈就是平时说的燕雀,这八种燕雀鸟,再加上一个老扈, 合起来就是九农正,因为这九种候鸟在不同的农时出现。
春天的鸟儿,提醒该播种了;夏天的玄色鸟儿,提醒该护苗了;秋天的浅蓝色鸟儿,提醒该收获了;冬天的浅黄色鸟儿,提醒该贮藏了;桑树上浅脂色的鸟儿,替蚕驱逐不坏好意的雀鸟;荆棘中浅红色的鸟儿,不让雀鸟靠近果子;白天唶唶叫的鸟儿,赶走庄稼地里的雀鸟;夜晚啧啧叫的鸟儿,赶走小动物;老扈鸟出来,提醒起床不要懒,早出工干活。

颜色色值的决定因素,除了色调,还有饱和度和亮度。
古人不会用数字去表示色值,但他们会巧妙地用字来表示色值,譬如“窃”“盗”“小”“退”“不 肯”都是表示浅色的意思。
自从知道窃蓝,我研究过不少浅蓝色的鸟儿:铜蓝鹟、红胁蓝尾鸲、黑枕王鹟、白眉蓝姬鹟。虽然不能考证秋扈到底是哪个鸟种,但是这些美丽的浅蓝色鸟儿还是让我开心了很久。
凝夜紫

凝夜紫,这个典故出自唐代诗人李贺的《雁门太守行》:“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燕脂凝夜紫。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李贺号称“鬼才”,擅长使用颜色词汇,一首诗就是一幅色彩画卷,凝夜紫的这首诗也是波诡云谲,诗名《雁门太守行》不过是借用古乐府的题目, 写的不是山西雁门,而是河北定州的战事。
元和四年(810 年)冬,成德军节度使王承宗反叛,宪宗任命宦官吐突承璀率兵平叛,战事不利,河北糜烂,《雁门太守行》说的是叛军围困义武军节度使张茂昭的驻地定州,守军固守待援。
黑云动,一点日光照到甲衣,金光灵动;角声起,几腔热血红过胭脂,紫塞呜咽。
西晋学者崔豹《古今注》有:“秦所筑城土色皆紫,汉塞亦然,故称紫塞者焉。”凝夜紫,解释成紫色边城不是不可,但我觉得解释为青紫色的初夜天色更合适,古诗有“赤帝当年布衣起,老妪悲啼白龙死,芒砀生云凝夜紫”(胡仔),“浮岚出晴丹,淑气凝夜紫”(石宝),说的是天色。

凝夜紫的实证讨论似乎可以归结到具象的颜色,诗歌的浪漫又可以归结到意象的颜色。更诡异的是李贺并没有亲临战场,这不是观象成色,一切都不过是他的想象,那年冬天,他一直住在东京洛阳仁和里东舍。
暮山紫

暮山紫,语出唐初文学家王勃的《滕王阁序》:“潦水尽而寒潭清,烟光凝而暮山紫。”王勃写《滕王阁序》是唐高宗上元二年(675 年),他二十五岁,文学神童的人生道路并不顺利,因为不顺利他也成熟了不少,这时的他还不知道自己差不多走到了人生的最后。
中国传统色的美学意境,往往是借由天地万物的具象,引发微妙、曼妙、隽妙的意象,从精致细微之时刻、诗意浪漫之感触、丰饶深厚之底蕴,而酝酿出独特的东方审美。
烟光凝而暮山紫,就是在黄昏的时刻,诗人观察到山间烟雾与夕阳落照的交织,薄薄的一层紫雾罩住了暮山,暮山见我,我见天地万物。
本文节选自:

《中国传统色:色彩通识100讲》
作者:郭浩